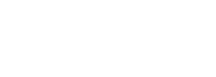“翠微校史”:西北楼里的大师们
2020/06/29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,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著、学养和品德,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,仍然依稀于眼前
所谓“翠微校史”,不知是谁冠以这样诗意的名称。而其所指,就是1963年从全国院校抽调专家学者,住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西北楼,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。
我的父亲赵守俨(注: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)从始至终参与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,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。1963年,我只有14岁,虽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,对文史有兴趣,但对点校二十四史是怎样的工作和过程,是完全不清楚的。只是由于我家住在翠微路的机关宿舍,与那些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,所以尚能从侧面回忆些当时的情景。
西北楼
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,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,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,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。
严格说,应该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从50年代末到“文革”前夕,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《宋史》出版,全部点校工作完成。
在第一阶段中,前四史的点校是整个工作的前奏。《史记》在顾颉刚先生点校的基础上由宋云彬先生再次加工整理完成;《汉书》是由傅东华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基础上加工完成,《后汉书》的点校主要是宋云彬先生完成;《三国志》的点校是由陈乃乾先生完成。1959年《史记》正式出版,其他三史也在“文革”前陆续出版。
至于其他各史的点校基本是从1962年开始的,而集中各地的学者到中华书局参加全面点校工作则是从1963年开始。
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,叫作西北楼和西南楼。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,西南楼是商务的宿舍,西北楼是中华的宿舍。每座楼都是三层,各有三个楼门,每层有三个单元房,两个三居室,一个两居室。房间的面积都较大,冬天的暖气虽然烧得不好,但是都有。
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中。西北楼一门和二门基本住满,只有三门里没有几家人,绝大部分单元都是空着的,够住二十几人。
从1963年初开始,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教授。家在北京的教授为了工作方便,不受干扰,也有住在这里的,但是不多。
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,人员的流动很大,你来我走,有的住的时间长,有的住的时间短,最多时十六七人,最少时只有七八位。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,里面有单人床一张,书桌一张,书架一个,衣柜一个,十分简单,类似招待所的性质。
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,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,工作条件较好,生活也算方便,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,条件相对好转。
当时没有煤气,中华书局职工和家属都要自己生炉子做饭,外调来的专家学者则不用做饭,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,到吃饭的时间,走几步就到食堂,坐在饭桌前就行了。那时我家虽自己做饭,但也常到大食堂去买些主食,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。鸡鸭鱼肉每顿都有,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、海参、对虾什么的,伙食相当不错。早点也有牛奶、豆浆、稀饭之类。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。
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专职工友高培义,是个个子不高、很憨厚的年轻人。因为单元里没有炉火,所以每天要及时给他们送开水。这位高师傅每天两三次给他们送水,一手提着四五个铁皮暖壶,穿梭于西北楼和大食堂之间。
每逢春节,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,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。
教授们
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,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,是金灿然先生发现他的才华和能力,让他负责古代史编辑组的工作,他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。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,也不过三十六七岁。但是,许多整理工作的规划都由他起草,加上他的家世背景和实际水平、工作能力,得到了那些老先生们的肯定和尊重。因此,他与各地来的专家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这些专家学者中,我印象最深的多是在这里住得较长的。如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、张维华先生、卢振华先生,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、陈仲安先生,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,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先生。家在北京的则是北大的邓广铭先生、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先生,还有就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宋云彬先生等。不过宋云彬先生并不住在西北楼,而是住在大院一区的一栋日式别墅中。当时《明史》的点校工作是郑天挺先生带着南开的教授在天津做的,不过郑天挺先生有时也住在这里。北大的王永兴先生后来是内子的导师,他也经常回忆起在西北楼的日子。
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很紧张,经常要伏案到深夜,几乎没有星期天。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,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。来得最多的是王仲荦、唐长孺和宋云彬三位先生。王、唐两位先生来此都是谈点校工作问题的,而宋先生来此谈完工作以后,聊的闲话也最多,甚至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