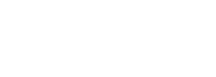西北有浮云
2020/10/12五月沙枣花开。“沙枣花一开,姑娘就想嫁人了。”每到这时节,维吾尔族老人都这么说。
他们说沙枣花的气味催情。
当枣果儿落在地上与枣花一起在泥土中发酵,那腥甜而腐烂的味道弥散整个南疆大地,让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留在这儿,就是被这股子邪气给困住了。
一
周六或者周日,吃过晚饭后,看严小宓穿衣打扮是我唯一专注的事情。
1984年的奎依巴格镇(注:奎依巴格,意为理想的花园)像南疆戈壁滩巨大无垠的叶片上的一小块疤痕,而这个年轻的女孩就住在这疤节的某一处平房,对镜佝腰,一遍遍在脸上涂抹着膏、霜、水、粉。美人鱼牌眼线笔、紫罗兰散粉等廉价的化妆品铺了一桌子。
这个时候,作为妹妹的我半卧在房间一角的旧沙发上,一会儿举着报纸大声念新闻标题,一会儿走来走去假装拿抹布擦桌子、擦板凳,可是眼睛时刻看着她在镜子前改头换面,看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镇女孩在散发着煤烟味的黄昏,怎样绽放成一朵塑料花。
要知道,严小宓在她的少女时代就有一种成熟妇女的气息。真正的少女不是她那样的。每到沙枣花开的时节,我在令人头晕的气味中想到了她。可是就这一点,深深迷住了当年天真无知的我。面对她,我时常像是自我惩罚似的,经常搜索我身体上的每一处丑陋:皮肤像失血似的苍白且粗糙,肥大的蒜头鼻上撒满了黑芝麻般的黑头白头,脸颊两边的法令纹很深,油腻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,看人的目光是怯怯的,总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。
我还经常伸手插进衣服里,狠狠挤捏滚圆肚皮上的一圈肥肉——个头不到一米五的我,当年的体重居然有一百二十多斤了。在漫长的青春期,一个过于招摇轻浮的姐姐,无疑压制了我追求美丽的欲望。
此刻,客厅墙上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严小宓的脸,也映照出我的脸。
严小宓当然知道我喜欢盯着她看,尽管她瞥都没朝我瞥一眼,但空气中某种颤动,仿佛从她顶得高高的、丰茂张扬的头发的天线传递了过来——那是她一身俗气的华美装扮给四周空气通了电,对我一遍遍地说:“你来看我吧,来看我吧,羡慕我吧。”
最后,她踩着一双腥红色人造革高跟鞋,骑上自行车前往小镇舞厅。
去往小镇舞厅的路上还有一些像她这样的女孩。当她们脂红粉白地走出家门,个个都画着自认为最好最美的、让男人们看了走不动的妆。她们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上,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鸟,给夜晚的小镇大街送来几分人间气息。
这一年暮春,奎依巴格镇第一家舞厅开业了。舞厅是由镇机关礼堂改造的。当舞厅的灯光越来越暗,越来越炫,对于边疆小镇的人来说,这种闪着五光十色的霓虹无疑是一种沉醉剂,一种时髦——三步、四步,快四慢四的舞曲换了一支又一支,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》奏出了热带风情,女人的裙裾如热浪,一点点地朝着舞厅的中心移动。又换了一支快四的舞曲,一条条裙子怒放,全场女人的长头发短头发在快节奏的音乐旋律中刮起了黑色旋风,成了兽鬃。白天那紧绷的肉欲在这一刻彻底松弛了下来,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舞动、旋转,像波涛一样要涌出封闭的堤岸。
在这些旋转着的女性当中,我的姐姐严小宓看起来是一个多么快活的人——是的,她跳舞的时候最快活,舞厅的男人们都接二连三地请她跳舞。她穿着俗艳的紫红色金丝绒长裙,露出白色钩花的三翻假领子,轻抚男舞伴的肩膀,眼神灼热,像似两汪热油。她人生所有的明媚,都在此刻尽情燃烧了。
舞会结束的尾声,转暗的灯光不断变换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,舞厅响起了歇斯底里的迪斯科音乐。我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都在变形,随着音乐汗水淋漓地肆意扭动着年轻的臀部,舞伴们之间相互拉扯着,好像生怕对方不小心变成了别人,拥挤的空间充满了烟味和令人头晕的体臭味——那是雄性与雌性动物在一起的味道。
有一次,我大着胆子跟着严小宓进了镇舞厅。那天,我穿着宽大的豆绿色卡其布夹克衫,而女孩们则穿着当时流行的长长短短的裙子。除了穿着,我发现我跟别的姑娘不一样,她们快乐、放肆,浑身散发出小镇姑娘的浮浅的风情,三五成群团在一起,时而爆发出莫名的笑声。而我脸色蜡黄,神态举止显得拘谨,可以说是束手束脚。
整个晚上,我缩在舞厅靠墙壁的一个小角落,为自己的寒酸和过时感到难过,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属于我,我只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罢了。舞池里,男女之间相互搂抱,欲退还迎的神态,又让我的心变得火热和蠢蠢欲动,竟有些喜欢这里的气氛了。
上一篇:西北角的小金刚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