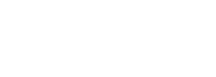河上春
2020/08/25爸爸去世后,乐玲晚上改搭同伴的车回家。这是她十年来换的第四家餐馆,门上很显眼的挂着“创立于1980年”的招牌。现在这种快时代,三十年已经相当于从前的一百年了吧。餐饮这碗饭吃久了,乐玲觉得都差不多,叫她做领班,工资还不错,也就可以了。头天去上班,同伴猜她不到三十。有这么年轻?“都快四十了”冲到嘴边又缩回去,更不想提在西北结过婚,不然十年前就不跟着退休的妈妈从西北回硖石老家,一心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了。她们一来,随后爸爸也跟来了,买菜,烧饭,晚上接她回家,直到突然过世。两个没离开过西北一步的叔叔接到消息坐火车赶来,先顺便去西湖逛了一天,第二天抱上爸爸的骨灰仍坐火车回去。直到那时她还不相信爸爸真的不在了,上下班进出餐馆,总疑心他在哪儿站着,慢悠悠抽着烟等她。他从不像妈妈那样不耐烦地催她相亲,怨艾地问她结不结婚了。他总帮着她说话,说,这要看缘分,没到时间,叫她碰上谁呢?
如今想起这些,她总感到心痛,看着车子拐过弯,从五光十色的餐馆门口开过去。边上的女孩撞撞她,问她去不去,她们想去洗脚,侍候别人一天,让别人也侍候侍候。
她们常去的足浴馆有两个技师长得眉目清秀,可妈在家等着她,有什么办法,所以叫同伴把车开到公交站边停下了。
走几步回头,已不见红色小标致。
不觉往外吐了一口气。一天来积在心里的一口浑浊之气。
随即,心里涌起难以形容的一阵轻松。
没有比劳累一晚上独自走在这里更轻松自在的了。
这小区租金便宜,是最早的教职工居住区,有妈所谓的书香气。妈总忘不了她的教师身份,到这儿却没交到教师朋友。这些老教职工不是没地方搬,就是恋旧不想搬,早睡早起,自有一套规律,很少理会她们这些“没文化”的外来人口。
要说也是,妈和她有什么文化呢?不过在此安个身罢了。
三角花坛那棵高大的云杉把四周遮得黑漆漆的,不免让她联想起让人惧怕的那些事件,“朱令案”啦,“南大碎尸案”啦,这些案子久久破不掉,成了悬案。前些时候白银案凶犯归案,又把这些老案子带出来。她为这些精英分子心寒,说他们做人这么冷酷无情,白读书了,妈抱怨的却是这里树太高,又不修剪,把路灯的光给挡了,还去社区反映过。这当然是没用的,好在边上有个平价超市,关门很晚,这会也不见买东西的人,望去只有一个浅浅的白影,在花坛边缓缓移动着。
这地方的男人斯文,灌她两杯,看她有醉态了,笑她两句,取点乐,就放她走了。她遇到过几个大客户,还对其中一两个动过心,现在她已经打消从他们中间找个人结婚的想法,寄希望主给她安排,每个礼拜去城南的教堂做弥撒。爸爸突然去世后,她的祈祷词又加上愿爸爸灵魂安宁,妈妈身体健康——她在想象中的圣母和耶稣恩泽万物的光环里,看着这个人忽然迎面朝她走过来。
不会认识我吧?来店里吃过饭?她刚这么问了自己一句,听着风声不对,头上已经结结实实挨了一棒。人扑到地上,包差点滑掉,幸亏她拽得快,可他更快更稳地把包拽住了。你!她瞪他,在痛极眩晕的状态下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
这儿是小区啊,也不怕让人抓了!她放声一喊,窗后探出几个脸。她像找到救星,喊得更响了。可那几个脸不管看没看明白情况,一律缩了回去,关上窗,灯也关了。这一分神,她更不是男人的对手,他下狠劲推她一把,挟着包三步两跳闪入一幢楼后。
等她爬起来光脚追过去,他当然早不见了。月季结着硕大的花挺立在月光下,也像栽种它们的老年女教师,带着刺激她的孤傲神情。她望着,不由淌下两行眼泪,好像被这些花瞧不起比刚才那顿打还难受。一边找着鞋子,一边摸回到花坛边,花坛里有光闪过,竟然是她的手机,马上拨110报了警,随即拨了家里的。
妈来的时候,警车也到了,下来一老三少四个警察。妈说下了楼又想起上去拿衣服,所以慢了,手抖着给她披上。她说不冷,话出口却带着齿音,就像带着咬牙切齿的憎恨,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。
年长的警察让她说说男人的年龄和穿着特征,竟把她问住了。
警察叫她再想想,“你信不信?信息够准,今晚就逮到。”
妈抱怨的仍是那几棵树,“我说这些树太高了,又不修剪……你们看,出事了不是?”
上一篇:贾植芳与西北 下一篇:没有了